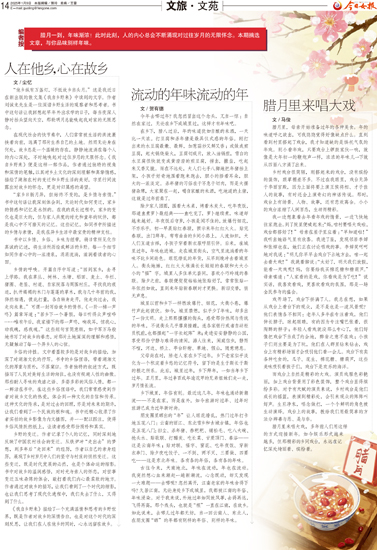今年去哪过年?我忽然冒出这个念头,兀自一惊:自然在家过,无论在乡下或城里过,这样才有年味吧。
在乡下,腊八过后,年的味道犹如自酿的米酒,一天比一天浓。打豆腐和杀年猪是最具仪式感的年俗。刚打出来的水豆腐最嫩、最鲜,加葱蒜炒又鲜又香;或做成煎豆腐,起大锅烧柴火,豆腐切成片,放入油锅煎,雪白的水豆腐很快就变成黄澄澄的煎豆腐,捞出,撒盐,吃起来又香又脆。而在不远处,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年猪抬上架,小孩子好奇地围着跑来跑去,胆小的捂着耳朵,胆大的一派淡定。杀年猪的习俗在于不急于切肉,而是大摆猪杂席,大家聚在一起,喝自家酿的米酒,吃地道的土猪,这就是过年前奏了。
除夕家人团圆,围着大木桌,烤着木炭火,吃年夜饭,那道鱼煮萝卜最经典——鱼吃完了,萝卜继续煮,味道却越来越好。年夜饭后守岁,小孩是闲不住的,放爆竹烟花,不亦乐乎。初一早晨贴红春联,预示来年红红火火。贴完春联,出门拜年。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,人流如织,大人们互道吉祥,小孩子穿着新衣服呼朋引伴。后来,在城里过年,年味也进城。走在城里街头,空气里流淌着的年味不比乡间逊色。眼花缭乱的年货,从早到晚冲击着城里人。街头地摊,红红火火堆满长长短短的春联和大大小小的“福”字。城里人多住单元套间,喜欢小巧玲珑的春联。除夕之前,春联便熨熨帖帖地张贴好了,常常张贴一年依然如故,直到来年贴新春联时才更换。新旧交替,悄无声息。
城里以前和乡下一样燃放爆竹、烟花,大街小巷,爆竹声此起彼伏。如今,城里禁燃,似乎少了年味,却多出了一份文明。走上熙熙攘攘的街头,感受那份热闹与传统的年味,不说街头几乎摩肩接踵,连各家银行或者自动柜员机前,也都摆起“一字长蛇阵”来;走进安安静静的公园,享受那份宁静与难得的清闲,游人往来,闲庭信步,静而不喧,河边、桥上、亭台轩榭、草地、假山,随意憩息。
父母尚在时,陪老人家在乡下过年,乡下老家似乎淡化为一个积淀着乡愁的记忆符号,留下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根之所系。此后,城里过年,乡下拜年,一如当年乡下过年。正月里,年过半百或年逾花甲的兄弟姐妹们走一走,岁月情长流。
乡下城里,年俗有别。最近这几年,年味也涌动新潮流——不是在家,而是在外,如今旅游时过年、过年时旅游已成为过年新时尚。
朋友圈里晒出的“年”让人眼花缭乱,热门过年打卡地五花八门:云南的丽江、东北雪乡和古城古镇,年俗也是五花八门:扫尘、杀年猪、舂粑粑、铺松毛、吃八大碗、抢头水、贴歌联、打醋炭、吃长菜、甘蔗顶门、春浴——这是云南年味;贴对联、福字、窗花、吃年夜饭、穿新衣串门、除夕夜吃饺子、一不倒、两不灭、三要做、四要吃——这是东北年味。各有各的年俗,各有各的年味。
古往今来,天南地北,年味在流动,年也在流动。我突然想心血来潮赶一趟新潮流,心念既动,却又发现一大难题——去哪呢?忽然离开,江南老家的年味舍得下吗?久居江南,无论身处乡下或城里,我都被江南的年俗、年味浸染。对于我来说,外地过年如同放风筝,去得再远,飞得再高,那个线头,也就是“根”一直在江南,在故乡。如此说来,去哪儿过年都无妨,当一回云南人、东北人,在朋友圈“晒”的年都有别样的年俗、别样的年味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