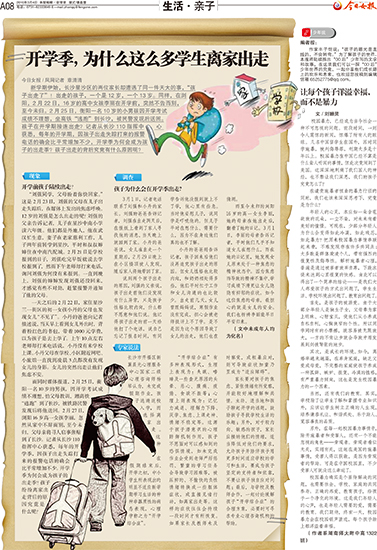中国人重乡情,行走在外若能听到熟悉的乡音,不说泪两行了,心中必是欣喜的。在异乡如此,在他国更是如此。一个地方的人的相同口音与习惯,是外人不懂的隐秘。中国各地方人的“欺生”,怕就是这么发展而来的,听说上海人尤甚。
记得我小时候每每接到来自长辈的电话,常常是兴高采烈地讲了许久,结果挂断后母亲问一句:“讲的什么?这么高兴?”如同浇了我一头冷水——我根本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,只是两个人都一问一答“聊”得很开心。不仅我是这样,身边有不少朋友也是这样。不过他们比我出息,他们这一代生出新的方言,还是带着地方浓浓的烙印,上一辈的老话也听得出来,但意思不全懂。
可令我惶恐的是,我越发感到我这一代文化的趋同性。不是指文化本身,而是指我们自己。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从故居迁往各地,这些人的后辈基本上很少能待在家乡,前人的“第二故乡”成了后辈的故乡。于是,原本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没有继承下来,别人的东西又没有学像,或是把别人丢弃的东西捡拾回来,拍干净,然后宣布是自己的。希望我的想法是杞人忧天,毕竟每个人的家族往上追溯都不一定是本地发源来的,据我家的家谱,我应是山东人。但可惜的是,当下一代问起的时候,我又能用这陌生的语调诉说我的家乡么?就像龙应台《目送》一书中出现的“爱己”,初读时怎么能想起老祖母的模样呢?(爱己即娭毑,湖南方言中指“奶奶”)
就算现状是如此,我还是无可救药地向往我的故乡。我会努力把父辈讲的故事一条一条地对应到山山水水中,这么说还夸大了,老城区的翻修使我迷茫:到底哪条路是我父亲年少读书时骑着破自行车经过的?到底哪一棵枫树是我母亲玩累时宿过的?没有东西能回答我,我看到的是马路边新栽的樟树,与河那边新起的高楼。
乡愁对我来说都是奢侈的享受,小时候总觉得思念催人心肝,现在才知道有东西思念方是幸福。没有归感感的人是可怜的。人如枯叶,永岁飘零。(作者系湖南师大附中1322班学生)
|